吾年二十有七,仍在情感的迷宫里打转。凡人的七情六欲是天生的枷锁,我挣不脱,也逃不开。日子越熬越钝,世间生活的艰难,让我对这个世界的期望,正一点点磨成齑粉。
“我们都对这个世界很失望,不是吗?”
一句沉重的话语从身后传来。我转过头,只见一个中年男人邋遢的形象映入眼帘。他头发油腻地贴在额头上,旧夹克的袖口磨出毛边,面色沉重得像蒙着一层灰,眼底全是人生的沧桑与疲惫。
我忍不住好奇地问他:“这么多年过去,你就不想回去看看吗?”
他眼中闪过一丝哀伤与无奈,缓缓开口:“那个家已经不再是熟悉的样子了,现在的我,自觉无颜面对家人。”他的声音很低,像埋在喉咙里的叹息,话语里全是对过去的眷恋和对现实的无奈。
我心中涌起一股同情,朝他抬了抬下巴:“走,颜某请你吃碗热的。”
他眼里闪过一丝惊讶,随即又被无奈和辛酸淹没,声音微微发颤:“多不好意思啊。”他的手在身侧攥了攥,指节发白——那双手布满裂口,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泥,一看就是常年干粗活留下的痕迹。在眼前的困境里,我们的沉默与疲惫似乎产生了共鸣,或许,颜某有一天会过得不如他。
街边正好有一家羊肉粉店,塑料门帘被掀开时,混着羊汤和辣椒的热气扑面而来。我点了两大碗,老板吆喝着端上来,粗瓷碗沿烫得人指尖发麻。
“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?我记得当年上学时你两次带女友回家,我们都以为你会过得很好。”
他端起碗,指尖摩挲着温热的碗沿,像是在积攒开口的力气。“一言难尽!”
“当年我跟她好的时候,觉得全世界就她最懂我。我把打工攒的几万块全给了她,还跟家里骗说要做生意,把爸妈准备给我盖房的钱也拿了出来。谁知道,她转头就把我骗去了北方的黑厂。”
“那地方根本不是人待的。铁门焊死,窗户装着铁栏,每天早上五点就得起来,在机器前站十二个小时。有次我手被机器卷了,老板只给我撒了点灰扑扑的消炎药,连医院都没送。晚上就挤在十几个人的大通铺里,臭虫咬得人根本睡不着。我想跑,被他们抓回来打得三天起不了床,还被锁在小黑屋饿了两天。”
“熬了三年,我才被解救出来。可身体早就垮了,一到阴雨天,整条胳膊都疼得抬不起来,有时候还会突然头晕耳鸣。更糟的是,他们给我灌过不明不白的药,我现在脑子时常犯糊涂,前一秒还记得要做什么,后一秒就忘了。”
“出来的时候我已经三十一岁了,找工作处处碰壁。人家看我脸色差,问两句病史,一听我在黑厂待过,还落下病根,连面试的机会都不给。我去工地搬砖,干了半天就疼得直不起腰;去餐馆洗碗,老板嫌我反应慢,第三天就把我开了。”
“我没脸回家。兄弟已经成家了,他们都以为我不在了,我把他们的养老钱都造没了,现在混成这副鬼样子,怎么敢回去见他们?有时候半夜醒过来,发现自己睡在桥洞底下,雨丝飘进来,冷得直打哆嗦,我就想,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?”
“有次我饿了两天,在街边捡别人吃剩的盒饭,被当成疯子赶。还有一回,我在地下停车场躲雨,保安拿棍子打我,骂我是流浪汉。我也想过好好过日子,可老天爷不给我机会。”
他说着,声音越来越低,最后几乎是哽咽着:“我现在就像个没根的草,飘到哪儿算哪儿。有时候看着街上的人,一家三口说说笑笑,我就觉得,这辈子是真的完了。”
我静静地听着,手里的羊肉粉早已凉透,心里却像被火烫过一样难受。我想起自己二十七岁的迷茫,想起那些在深夜里独自崩溃的时刻,原来在命运面前,我们都不过是在泥里挣扎的人。
我拿起桌上的辣椒罐,给他碗里添了半勺辣,又把自己碗里的肉片夹了几片过去:“我懂那种‘老天爷不给机会’的感觉。我二十七岁了,没房没车,连个能说说话的人都没有,有时候走在街上,看着别人的热闹,也会觉得自己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”
“但刚才听你说的时候,我突然想起我爷爷讲过的一句话——‘人这一辈子,就像熬汤,熬到最苦的时候,再添一把火,说不定就香了。’你能从黑厂熬出来,能撑过那些桥洞和冷雨,就已经比很多人强了。”
我看着他发红的眼眶,声音放得更轻:“你不是没根的草,你只是暂时被风吹离了土壤。要是哪天想回家了,就回去看看吧。爸妈要的不是衣锦还乡的儿子,是能平平安安站在他们面前的孩子。以后有什么打算吗?要是想回去,颜某给你找个车送你回去。”
“不,不了,玄策如今这副模样,无颜面对父母兄弟姐妹。谢谢你请我吃饭。”他低着头,把碗里的粉扒得飞快。
“光说我了,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?”玄策忽然抬头问。
“我啊,混得很不好。”我笑了笑,指尖在凉掉的碗沿敲了敲,“小时候上学成绩一塌糊涂,乡里乡亲都说我不是读书的料,父母亲戚也跟着附和。每次他们凑在一起聊谁家孩子成绩好,我就像个见不得光的过街老鼠,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”
“其实我心里清楚,从小学一年级起,命运就给我挖了个坑。那个叫顾欢的女孩,总在上课的时候拉着我玩橡皮、传小纸条,我刚想认真听老师讲课,就被她打断。就这么稀里糊涂混过了一年级,到了二年级,爸妈想让我留级,可学校不让。从那以后,我的成绩一路往下滑,再也没跟上过。”
“慢慢地,我成了家里和学校里的‘反面教材’。只要大人聊起学习,我的名字就会被拎出来当例子。上了初中更是没人管我,初二那年我干脆辍了学,去了职校。本以为能学个一技之长,没想到那地方就是个‘收容所’——老师不管,学生混日子,我待了两年,除了打游戏什么都没学会。”
“后来出了社会,我咬着牙想拼一把,先是开网店,白天蹲在批发市场选货,晚上熬夜修图、回复消息,可不懂运营,半个月只卖出两单,最后压了一堆货在出租屋里,连房租都交不起。不死心又去做自媒体,买了二手相机拍短视频,蹲在街头拍了一个月,涨粉不到一百,最后连买内存卡的钱都没了。听说3D打印赚钱,我又东拼西凑借了钱买机器,结果因为不懂技术,打出来的模型全是残次品,最后机器只能当废铁卖掉,还欠了一屁股债。”
“看着曾经要好的朋友,有的开着车带着家人自驾游,有的在朋友圈晒结婚照,而我还在为下个月的房租发愁。有次我去参加同学婚礼,被人问起‘现在做什么大生意’,我只能端着酒杯苦笑,说‘还在混日子’。那天晚上我走在回家的路上,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,我突然就懂了,原来有些人的人生,从一开始就注定是烂牌,再怎么挣扎,也赢不了这该死的命运。”
“我记得你不是有个很要好的青梅吗?你们走到一起了没有?”玄策问。
我夹粉的动作顿了顿,喉结滚了一下:“小时候我也这么觉得,虽然没上初中之前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。她总爱跟在我身后,喊我‘小安哥’,把攒了好久的糖塞给我。可上了初中之后,我就越发觉得自己配不上她——她是全年级前三名的尖子生,老师捧着,同学羡慕着;而我是连作业都交不齐的差生,走到哪里都带着一股‘烂泥扶不上墙’的味道。”
“我开始故意疏远她。放学绕开和她同路的巷子,她发来的消息我隔天才回,甚至偷偷把她的备注从‘小青梅’改成了‘表妹’,就怕她看到我藏在心底的自卑。我想,这样她就会明白,我们只是普通亲戚,她值得更好的人。”
“后来她真的不再找我了,听说她谈了个很优秀的男朋友,再后来就收到了她的婚礼请柬。婚礼那天,我帮着端盘子传菜,还随了三百块钱。没人知道,我站在冷风里,手里的烟蒂烫到了手指都没察觉。那天晚上我回到出租屋,把她小时候送我的糖纸翻出来,一张一张铺在桌上,就像把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,全都摊开在眼前。我表面装得满不在乎,心却像被钝刀反复切割,疼得连呼吸都在发抖。”
“我们都有自己的苦楚,不要灰心,你以后肯定会遇见更好的。”玄策低声说。
成年人的世界大概就是这样吧,没有更多的话语,简单几句话就能道尽很多不言而喻的事。
“颜某要走了。”我把最后一张纸币拍在桌上,声音很轻,却像块石头砸在这满是油污的桌面上。
“去哪儿?”
“不知道,走到哪儿算哪儿。”
“多谢你请我吃饭。”玄策说到。
我转身掀开门帘,外面的风裹着雨丝扑在脸上,冷得人一哆嗦。身后羊肉粉店的暖光和热气被门帘隔绝在外,就像我和玄策的人生,终究是要各自走进自己的风雨里。
他有他的黑厂旧伤和无颜归乡,我有我的烂牌人生和未说出口的遗憾。我们都是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的人,没谁比谁更容易,也没谁能真正救赎谁。
或许成年人的相遇,就是这样——在一碗热粉的时间里,交换彼此的伤疤,然后各自继续赶路。后来的某一天才听说,那天晚上,那个离家十几年的邋遢男人回了家,没两天,又消失在了茫茫人海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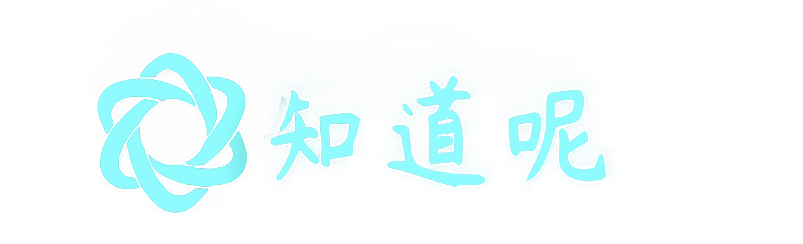


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